
投稿人:苏瑾(化名)/35岁/女生
苏瑾找到我咨询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。她是一名小学教师,三十五岁,语调温柔,声音里带着一种常年与孩子相处养成的耐心和包容。
“小玛老师,我……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”她深吸一口气:“在学校,孩子们都叫我苏老师。但我心里……还住了另外一个人。”
苏瑾的生活,是标准的“别人家的人生”。她从小就是模范生,听话、懂事、成绩优异,奖状贴了满墙,从小到大都是“你看人家小苏”。苏瑾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一所重点小学,成为深受学生爱戴和家长信赖的班主任。她的世界,由教案、红笔、孩子们的欢笑和“为人师表”四个字搭建而成,严谨、有序,且光明磊落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,这份“光明”之下,藏着什么样的阴影。
“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倾向,是工作第一年偶然看了一部小说。里面有角色被命令的情节,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”她声音很低:“那种感觉……让我特别害怕,就像心里某个从来没被敲过的门,突然“咚”地响了一声,我不知道是该开门还是假装没听见”。从那以后这么多年,她把这种“不该有”的渴望死死埋起来,用拼命工作和社会认可的“优秀”去压住它。她也试过谈恋爱,对方是个门当户对的公务员。但每当对方试图亲近,她身体就会变得僵硬:“我的心里疯狂喊放松啊你!但身体却诚实地在说莫挨老子。我不是不喜欢他,我只是……无法投入。我觉得我像个骗子,这让我没办法进入到恋爱和婚姻。”
“一次校内的培训。主讲人反复强调——教师必须是学生的道德楷模,言行举止皆要合规合矩。那句合规合矩,让我脸唰一下就白了。”
苏瑾就是在那样绝望的境地里,摸索着进了圈子。她在网络论坛上小心翼翼地发帖,字斟句酌……终于,她遇到了一个Dom,对方起初表现得极有耐心和风度,理解她的职业压力,表示愿意带她慢慢探索。然而,当她第一次实践后,巨大的罪恶感便排山倒海般袭来。
最让她感到恐惧和羞耻的,是她的身体反应。在那些私密的时刻,她的生理竟然诚实地回应了那种她理智上全力否定的感觉——一种混合着屈从、释放与巨大安宁的复杂体验。这种“愉悦感”在她看来,是最大的背叛。事后,汹涌而来的罪恶感会成倍地反噬她。“我竟然从那种……行为中获得了满足?我是不是骨子里就是个卑劣的人?”这种自我诘问,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内庭审判,而她既是法官,又是罪人。
“结束后回到家,我看着镜子里的人,觉得自己无比肮脏。”学校里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夜晚那个卑微的自己在她脑中疯狂交织,她产生一种强烈的失真感,仿佛灵魂被劈成了两半,哪一半都不再完整。白天我教他们要自尊自爱,晚上我却……我无法面对自己,我觉得我背叛了我的职业,不配再站在讲台上。”这种撕裂感让她痛苦万分。她既无法从那种渴望中获得真正的释放和安宁,又无法彻底割舍它回归“纯粹”的教师身份。她卡在中间,进退维谷,自我憎恶达到了顶点。
她变得无法直视一些词语。课堂上,当她带领学生朗读课文,念到“尊严”、“高洁”、“榜样”时,这些词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烫着她的喉咙。她觉得自己的声音虚伪至极。她甚至无法再坦然地说出“跪下”这个词,即使在讲解字义时,也会心跳加速,匆匆带过,仿佛那是一个与她有着肮脏秘密联络的暗号。
“站在讲台上,我是苏老师,我指尖捏着粉笔,勾勒出横平竖直的汉字,传递着世间最‘正确’的道理——真、善、美、诚实、自尊。孩子们清澈的眼睛崇拜地望着我,仿佛我是所有这些美好词汇的化身。然而,某个瞬间,或许是弯腰捡起一支掉落的铅笔时,裙摆摩擦过膝盖的触感,会突然让我像被电流击中一样,恍惚间拽回那个夜晚——那个被要求跪在冰冷地板上的夜晚。两种记忆的画面粗暴地叠加,让我必须用尽全力,才能将那个‘她’死死摁回心底的囚笼,维持着讲台上的镇定自若。”
苏瑾的痛苦,根源在于她无法整合自我的不同面向,陷入了苛刻的“自我概念清晰性”危机。社会赋予她的“教师”角色,带有极强的道德光环和公众期待,这与她私下隐秘的、被污名化的BDSM倾向形成了尖锐的冲突。她将这两种身份完全对立起来,认为它们是水火不容的。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,导致了剧烈的内心冲突和自我贬低。
她的问题不在于她的倾向,而在于她无法接纳一个完整的、多维度的自己——一个既是受人尊敬的老师,也可以拥有私密偏好的人。这种不接纳,源于内心深处对“完美人设”的执著,以及对社会眼光的过度恐惧。
小玛必须强调,BDSM偏好是成年人之间私密、自愿的探索,它本身不涉及道德评判,更与一个人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专业能力和人品无关。
圈内需要抵制一种错误的观念,即认为拥有某些偏好是“肮脏的”或“低人一等”的。真正的健康环境,应该鼓励成员实现自我接纳,将BDSM作为自我探索的一部分,而非分裂自我的根源。同时,也需极度警惕隐私保护,让成员不必担心社会身份的暴露。
“我和那位Dom结束了。不是因为他不好,而是我意识到,我首先需要面对的,是我自己。”苏瑾告诉我。
然后她和我开始了漫长的咨询,这从来不是帮她“消除”倾向,而是学习“接纳”自我。一个完整的人,可以同时包含“教导”与“服从”,“社会我”和“私密我”。它们并非对立,只是你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面向。
现在的苏瑾,依然是她那个学生们爱戴的苏老师。但她开始学习在私下里,不再那么尖锐地审判自己。“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再次尝试进入一段关系。但我至少学会了,在夜深人静时,不再带着憎恶去看镜中的自己。”她笑了笑,笑容里仍有涩然,但多了几分释然,“我不再觉得那是两个人了。那都是我。一个……稍微复杂一点的我。”
小玛深知,活在社会的期待里,是一场漫长的负重行军。我们被贴上各种标签,却常常忘了,真实的自我,远比任何标签都复杂和生动。真正的道德,不是活成一个毫无瑕疵的圣人,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,并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,安顿好内心的每一个部分。你不必撕掉社会赋予你的标签,你只需知道,那并非你的全部。请允许自己是一片有沟壑、有阴影、但也接纳阳光的原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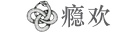 瘾欢
瘾欢